今年是乔治·索尔蒂(Sir Georg Solti)逝世10周年。这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红色与白色的血腥战斗,经历了纳粹大屠杀,经历了整个冷战时期,先后拥有匈牙利、德国和英国国籍,几乎搞不清楚自己属于哪个国家的犹太人,最终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指挥家之一。
1997 年9 月5 日,85 岁的乔治·索尔蒂跟往常一样,早起,泡咖啡,然后仔细校对完《索尔蒂回忆录》的最后几页。几小时后,他的妻子突然发现,大师已安静地辞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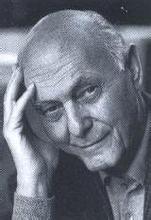
临终前半年,他仍辗转在9 个城市工作,并挤出时间写回忆录。这之后,他本来还准备大干一番——他计划在1998 年的演出现场录制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还计划录制全套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雅纳切克歌剧……
死神终止了这一切。人们把他送回祖国匈牙利,举行隆重的国葬后,他跟自己的导师、匈牙利最伟大的作曲家巴托克葬在了一起。
“匈牙利虽小,却是个伟大的国度。19 至20 世纪,这里涌现出了很多杰出的音乐天才。”索尔蒂逝世10 周年之际,匈牙利著名钢琴家、李斯特音乐学院教授巴拉斯·索科莱正在上海,担任第8 届弗兰兹·李斯特国际钢琴比赛亚太区选拔赛的评委。对记者提及索尔蒂时,他显得非常自豪。他将索尔蒂的成就跟匈牙利音乐史上的巨匠巴托克、柯达伊等人相提并论:“他们的存在让我觉得,身为匈牙利人,是一种极大的骄傲。”
犹太人中的幸存者
索尔蒂曾说自己的故乡匈牙利是一个“人们生活和呼吸在音乐中”的国度。他的家族原姓“斯特恩”,直到父亲这一辈,大部分人都是农民、面包师和磨房工人。具有音乐细胞的母亲,在索尔蒂6 岁时发现他“唱得很清楚而准确”,就此为培养他而奉献全部精力。
1877 至1890 年间,是匈牙利音乐界“群星闪耀”的时期。巴托克、柯达伊、利奥·威纳、艾尔侬·多纳伊,这些现代音乐史上响亮的名字,正是索尔蒂12岁考入李斯特音乐学院时的各科老师。“直到今天,李斯特音乐学院仍延续着严谨传统的校风,成百上千的学子进入这个殿堂,接受的都是最严格苛刻的训练。”身为教授的巴拉斯·索科莱说。
索尔蒂十多岁时,曾现场聆听拉赫马尼诺夫、霍洛维茨等人的音乐会,那时候,这些大师也不过二十出头。14 岁时,他被艾利希·克莱伯指挥的一场《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所震撼,“就像被雷电击中一样”,这个夜晚,他感觉“自己的命运被决定了”。
19 岁从音乐学院毕业后,索尔蒂先是到布达佩斯歌剧院做排练指挥。直到晚年,他仍认为这8 年历练是他走上职业指挥家生涯的最佳途径。这段“打杂”经历,让他见识到什么是好的音乐演绎。
1932 年,索尔蒂刚转到德国卡尔思鲁厄的剧院即被解雇。他黝黑的皮肤和浓密的头发决定了他的命运——作为一名来自东欧的犹太人,德国反犹情绪的滋长使得他不可能站上指挥台。次年,希特勒的上台使大量犹太籍音乐家相继失业,沦落至欧洲其他城市。
二战阴云将索尔蒂的未来推向深渊。德国吞并狂潮席卷欧洲,数十万犹太人被关进集中营,索尔蒂流亡到了瑞士。因为饥饿,他顾不上饭店门口“犹太人禁止入内”告示的威慑,用生平最快的速度解决午饭;坐火车穿越德国时,他因为担心纳粹上车查出他的犹太身份,“始终处于极度恐惧中”。
“如果我在战争初期回到匈牙利,我会像大多数匈牙利犹太人一样,不到战争结束就死了。”二战最后14 个月,他在匈牙利的家庭确实是一幅恐怖景象:父亲病逝,母亲常年藏于地下室导致精神失常,姐姐远躲他乡,被迫参军的姐夫暴毙于战场的严寒中。这段时间内,仅匈牙利就有60 万犹太人被屠杀。
“在那些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希特勒以及随之而来的大屠杀和成百万上千万各民族颠沛流离的无辜黎民百姓当中,我已经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了。”在回忆录的后记里,临近生命终点的索尔蒂对60 年前的经历依然心有余悸。
无国籍者的流浪史
对于“如何取得指挥经验”这种问题,索尔蒂给年轻人的答案总是“缠住他们,直到有人给你机会为止”。
1942 年,索尔蒂靠这种方法取得了在日内瓦大剧院指挥的机会,但却感觉糟糕——不懂法语,没时间研究总谱,排练时间少,使得歌剧《维特》的演出成为他“一生都在试图忘掉”的经历。让他声名鹊起的反倒是1942 年日内瓦钢琴大赛。虽然拿了冠军,但这次经历却使他坚信自己无法当一名钢琴家——比赛当天,他在上场前将贝多芬奏鸣曲中的一段赋格忘得精光,急得他想要退出比赛,却被工作人员推上了舞台。他的记忆空白在台上奇迹般消失了,但直到捧起奖杯,他仍惊魂未定。
1945 年二战结束,索尔蒂无法回匈牙利,那儿尚处于水深火热中;他也无法去美国,那儿有太多的欧洲指挥家在“抢饭碗”。要当指挥,他只有去德国,处于战争废墟中的德国人渴望恢复家园和他们的音乐生活。面对这个曾残忍屠杀自己同胞的国家,晚年的索尔蒂说: “我想我就像浮士德,为了能当指挥,与魔鬼签订协议,随他下到地狱。”
他在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待了6 年,在法兰克福歌剧院待了9 年,为战后德国音乐生活的重建作出了巨大贡献,甚至获得了德国国籍,却始终无法摆脱颠沛流离的异乡客的感觉。1960 年,当伦敦皇家歌剧院向他发出邀请时,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告诉他:“我们老一代的指挥,指挥不了歌剧了。你们年轻一代必须肩负起传统并把它传给下一代。你就是纽带。”事实证明,索尔蒂这根“纽带”不仅传承了托斯卡尼尼、富特文格勒等老一代指挥家,也提携起了当今世界上许多杰出的指挥家,如祖宾·梅塔(1960 年由其推荐至维也纳爱乐乐团)和巴伦博伊姆(1973 年由其推荐至巴黎交响乐团)。
他以喘不过气来的日程,规划了皇家歌剧院未来3 年的演出季。83 岁的世界著名男高音卡洛·贝尔贡齐前不久来上海举行大师班时,用“从未见过的精益求精”来形容索尔蒂。贝尔贡齐曾与这个“一生都充满激情的人”多次合作,并曾“联手”在皇家歌剧院闹出一次著名“笑话”。当时,索尔蒂邀贝尔贡齐演出威尔的歌剧《命运之力》里的男主角,但不尽如人意的服装和布景,使贝尔贡齐在演出中意外弄落了假发,引得满堂倒彩。贝尔贡齐说:“索尔蒂是一位容不得半点差错的人。他对艺术的要求之高,在指挥家中也是罕见的。”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索尔蒂喜欢跑去台下坐着,像观众那样聆听,“而其他大多数指挥家都认为,只要站在乐队前就够了”。
世界主义者的激情与梦想
在索尔蒂铺陈出一份宏大计划时,关于他“傲慢、专横”,“性情暴躁”的评价也同时涌来。国人可能一厢情愿地认为那些世界知名的大歌剧院都很“艺术”,观众都很“高雅”。但就算是在皇家歌剧院,反对索尔蒂的拆白党照样坐在顶楼喝倒彩,向他扔白菜,在他的车位上写“索尔蒂滚蛋”。
索尔蒂也不否认他跟乐团之间的糟糕关系。他用“非常不愉快”来形容自己跟纽约爱乐的相处;在维也纳爱乐,他精力充沛的个性也跟漫不经心而又心高气傲的演奏家们格格不入,甚至有小提琴手在排练中以离席来与他对抗。上个月访华的匈牙利著名钢琴家、指挥家佐尔坦·柯切什(Zoltan Kocsis)曾与索尔蒂交往多年,他告诉记者:“索尔蒂是个话少而精简的人,很少流露自己的感情……像索尔蒂那样能把任何一个乐团的水平发挥到极致,没有强硬的手段,几乎是做不到的。”巴拉斯·索科莱则指出:“做一名指挥,既要有音乐天才,又要懂得组织人才,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有时候这种心血比在音乐上付出的还要多。”他认为,索尔蒂的倔强脾气实际上只针对艺术:“他以艺术的标准去衡量一切,而把人情放在第二位。”
索尔蒂把与维也纳爱乐的合作视为“残酷的伤害”,但他们却共同为唱片工业史留下了一部巨作——世界上第一套历时15 小时的完整版立体声《尼伯龙根的指环》。直到今天,这套唱片仍被全球爱乐者奉为至宝。
索尔蒂曾说:“10 年的皇家歌剧院生涯,使我从一个中欧来的音乐家变为一个世界主义者。”1971 年,当他正式离开科文特花园前往芝加哥时,皇家歌剧院正如他就职时宣称的那样,以33部歌剧演出的辉煌数字成为世界歌剧院的翘楚。最初憎恨他的人们向他表示感激和敬意,英国授予他“大英帝国爵士”和英国公民身份。在此之前,索尔蒂保持了20 年德国公民身份。他对《时代周刊》说:“我的祖国只有一个,护照却有好几本。其实,我真正的国籍是音乐。”
索尔蒂接手时的芝加哥交响乐团负债50 万美元,士气低落,内部矛盾激烈。第一年,他就开始全力复苏广播音乐会、寻找赞助、提高乐手薪资,把马勒、布鲁克纳、斯特拉文斯基、巴托克的作品带到美国人中间,开发美国唱片市场。他每天都在疯狂工作,一周演出4 场音乐会,排练4 次新曲目,还要大量研究。他的到来,使乐团成为“一个马戏团或古代的军团”。18 个月之内,他们走遍欧洲10 个城市,并延伸及亚洲。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成功上演马勒《第五交响曲》之后,“观众全部都站起来,发出震耳欲聋的狂热呼喊,就像在摇滚音乐会上一样”。索尔蒂说,那是他一生从未经历过的眩晕场面。
芝加哥的岁月把索尔蒂的事业推向顶点。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欢呼和爆棚。澳大利亚建国200 周年庆典时,悉尼人以“两百年的企盼”横幅来迎接索尔蒂。乐团成员在他75 岁时送他的礼物,是有每个人签名的镜框,里面写了一句让索尔蒂感觉自豪的话:“你不仅是我们的大师,也是我们的朋友。”
1991 年,79 岁的索尔蒂发着高烧,举行了告别芝加哥交响乐团的演出,跟他合作的是帕瓦罗蒂。退休后的索尔蒂生命力更加旺盛,不但继续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还多年担任萨尔斯堡音乐节总监,并持续与维也纳、阿姆斯特丹、柏林、科文特花园等世界顶级乐团和歌剧院合作演出。70 岁之后,他总是把自己多年前的录音拿出来,一边听,一边对着放大复印的总谱,一句句研究。他说:“从这时起,对话在我们之间展开,仆人和主人。我感到自己对音乐的理解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